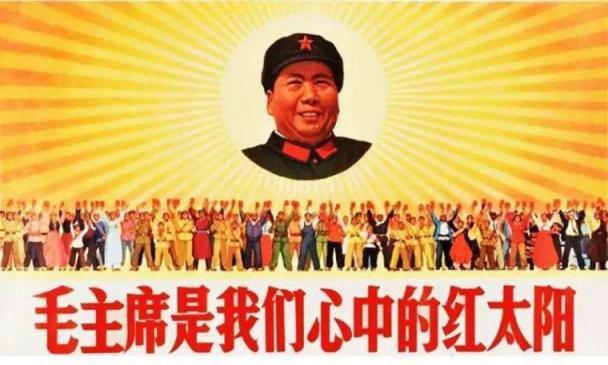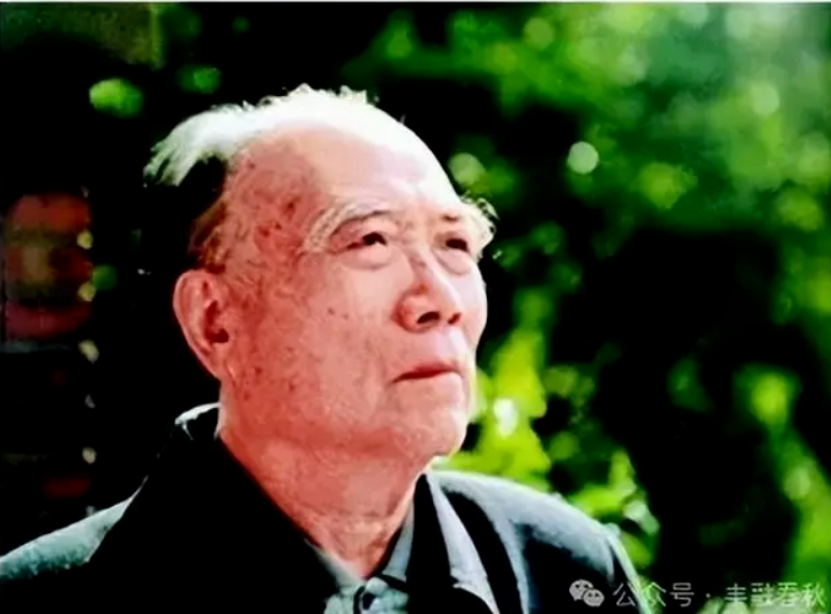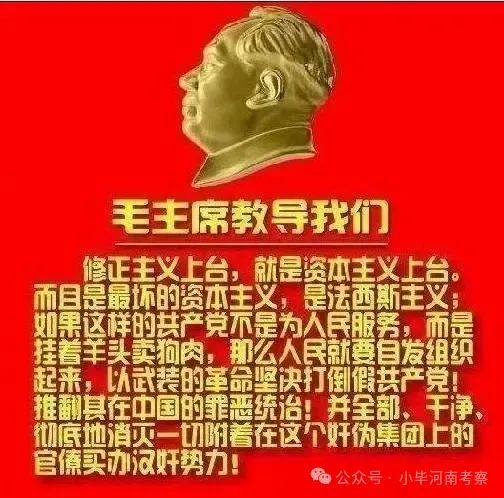左翼文学不死,左翼精神永存——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
文/李 季
如果用一种创作上的倾向来形容“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传统应该是这样一种传统:它以骨肉相亲的姿态关注底层人民和他们的悲欢,它以批判的精神气质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现实和不平等,它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呼唤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代表一种思想政治倾向的“左翼文学”传统,从上世纪20-30年代以先锋姿态出现开始,经过延安文学、解放后到文革前的17年文学再到文革文学,它经历了从“异端”到“主流”,又从“主流”复归“边缘”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一直处于被压抑、被冷落的状态,这其中有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但无论如何,“左翼文学”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经过半个世纪的体制化的灌输,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处,成为集体无意识,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现实,在当前和未来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继续提供给我们资源性的东西。今天,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下,左翼文学这种“异类”的声音,更表现出它的意义和价值。
曹征路的《那儿》(发表于《当代》2004年第四期)就是一部具有“左翼”精神气质和血统标识的作品,也堪称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现实问题,而且在艺术上颇有力量,给人以强烈震撼。
小说描述的是某矿机厂工会主席“我小舅”试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失败后自杀身亡的故事。小说中的工会主席“我小舅”是一个孤独的工人领袖形象,在他周围环绕着诸多矛盾:他反对“化公为私”的改制,力图阻止厂领导和将入驻的企业主无耻的贪污掠夺行径,不断上访;他是工会主席,是“省级劳模、副县级领导”,与普通工人有隔阂,不能“代表”他们去反抗;他的家人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劝阻他去反抗,这是他与小市民的庸俗自保思想的冲突。在反抗与“不能反抗”的痛苦挣扎中,他最终身心交瘁,只能选择了自杀。
小说还塑造了下岗女工杜月梅、小市民“我妈妈”、“我舅妈”等人物,而义狗罗蒂的形象尤为鲜明,它忠于主人而被驱逐、最终自杀的命运,与“我小舅”的遭遇具有同构性。小说以“我”的视角描绘出了一个以功利世俗为意识主导的现实世界,其中不乏知识分子的反省与无奈,这一视角的选择具有“复调小说”的某些特征,通过作者、叙述人、主要人物的相互间离,使作者的复杂态度得以呈现,而褒贬则暗寓其中:比如写到罗蒂和小舅的笔调是温情和理想化的,写到“我”和“我父母”等人物时略为嘲谑,写到“顺时人物”西门庆和媒体领导们时则是尖刻辛辣的嘲讽,更加深了作品的悲剧气氛和象征意义。鲜明人物形象的塑造,“复调”笔法的运用,都使小说摆脱了一般“问题小说”的简单化,而在艺术上具有较大的价值。
与其它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以“分享艰难”的姿态站在政策制订者一边来强调国企改革的历史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的被压抑、被损害的命运和显然是力量悬殊的抗争。如果说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80年代的“改革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结束过去,朝向未来”的现代性神话,《那儿》所书写的就是这种现代性的代价以及对这种现代性的置疑和反思;如果说以《大厂》为代表的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讲述的是一个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分享艰难”的故事,《那儿》要说的则是这种艰难最终却由底层人民来默默承担。小说描写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下岗工人们的抗争和反抗。小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新阐发、对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现状的揭示,可以看作“左翼文学传统”在今天的延续。
小说更通过主人公“小舅”的家庭出身把这种抗争和反抗与中国革命史上的工人运动相联系(主人公“我小舅”的外公是一位早已牺牲的革命烈士,解放前专门从事工人运动),从而暗示了这种反抗的“合法性”和历史必然性,暗示了社会主义历史及其赋予的阶级意识在今天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不仅使得作品带上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情感倾向,而且具有了与当下文学不谐的某种异质性和反叛性。具有特别意味的是,这种异质性和反叛性不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少数精英分子的反叛,而恰恰是大多数人的异质和反叛。这让我们确确实实闻到了历史深处的某种气息——“左翼”文学传统的气息。“政治家关注历史的车轮呼啸而过,文学家却必须关注车轮碾过的那一抹鲜红”。或许如小说所言,“小舅”的鲜血最终被历史的大雪所掩盖,文学却必须记载这鲜血、这掩盖和伴随这场大雪飘落的彻骨的寒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注和讨论这篇小说的价值。可是,我们还必须追问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篇小说会受到我们的关注?它满足了我们怎样的期待视野?
如果说,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能为读者提供一面意识形态询唤之镜,使我们每个人在这面镜中照见自己,那么,对一篇现实主义小说的关注,必然投射着读者的某种现实情怀,寄托着某种共同的情感体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最近因“郎咸平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指出有些国有企业改制“对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蚀”,“为了制止或纠正这些他们认为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剥夺,他们甚至开始用对抗的方式进行抗议”。这些都对“私有化”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思路不无反省意识。《那儿》是对这种反省意识形象化的呈现。它把反思国企改革这样一个敏感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命题,变成了作品中如临其境的对这个“过程”的描绘。
纪录片《铁西区》描绘了东北一个重工业区衰落的景象,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耗尽了能量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一起被抛弃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地位也走到了黄昏。《那儿》以个人悲剧性的抗争,展示了被抛弃者在这一过程中的绝望,更将这种绝望与抗争演绎成一曲盘旋在作品中的“英特纳雄奈尔”的主旋律。
当小说结尾处,绝望的“小舅”用空气大锤砸碎了自己的头颅,一曲久违了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英特纳雄奈尔》再次在我们的心中响起。小说的标题“那儿”就来自于“英特纳雄耐尔”最后两字的口误。显然,作者是想向我们暗示这样一个问题:“英特纳雄奈尔”所蕴涵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想及其实践,作为一种保护性力量,是否能再次成为我们借用的历史资源,为现代性的发展开辟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儿》的人物描写带着“左翼文学”特有的神性光辉。“小舅”这个人物似乎一开始就具有理想主义的本质:不考虑个人利益得失,一心为工厂和工人利益着想。就连他的亲人“我”看来,这“也太崇高、太伟大了,所以我不太相信。”小说多次描写“小舅”神话般的传奇经历:他文化不高,但胆识过人,青年时代当技工时就曾有过为国争光的辉煌历史,而他北京上访的经历则可谓智勇双全。在维护工人利益和保护国有资产上,他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终以自杀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理想。小说提到“小舅”的脸上有“一种神性的光辉”,提到他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使命”,更借用下岗工人组成的教友会里歌颂主的赞歌来赞美“小舅”。显然,作者是把“小舅”当成了工人阶级的救世主来描述。面对超越凡俗的“神性光辉”,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真实一旦和信仰相联系,它就不再存在于我们的感觉里,而存在于我们的理想和希望之中。如果一种关注现实的文学不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希望、寄托我们的理想,那我们是否需要这种文学?小说感动我们的,恰恰是这些对凡俗生活的超越。
这样强调《那儿》的阶级立场和倾向,也许会让人忽略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事实上,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特别是优秀作品,都不可能简化为某种单一、纯粹的意识形态,《那儿》也是如此。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小说中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立场:“小舅”的理想主义式的抗争立场,“我”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立场,“我妈”和工人们所代表的民众立场。对于“小舅”的似乎是螳臂挡车的反抗,我先是一副见怪不怪的不以为然,“这种事早就不稀奇了,连新闻价值都没有,矿机厂要是以一块钱转让那才叫新闻”。但逐渐,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发现我也染上了某种宏大的毛病,我居然相信小舅能带回一点好消息回来,居然”。而“我妈”代表的市民的态度则是,“谁爱贪就叫他们贪去,他能把长江水都喝干吗?咱们安安分分过咱们的日子”,“这年头没有是非只有利益,谁出头谁倒霉”。这些立场互相交织并试图说服对方,终于因为“一种绝境中生存的本能”,抗争立场占了上风。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最终对小舅的认同和赞赏,体现出作者的某种民粹主义倾向。小说中写到,股权认购风波后,“我”离开报社,选择了在工地上做民工,“什么也不想,只是为当天的工钱担心。”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批判现实的故事,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走向底层的故事。
虽然作者在谈到小说的写作时声称,“不要形式,不要技巧,只要说出皇帝新衣真相的那一点点率真”,但正是这“一点点率真”使得小说获得了成功。当红男绿女的欲望书写充斥着整个文坛,曹征路走向了当下和底层,并以切肤的疼痛说出了被忽视的和被压抑的真相,这就是曹征路感动我们的独特魅力。
我愿意把《那儿》称为一部单纯的作品。正因其单纯,它保留了锐利和锋芒。只是,这种锐利和锋芒,在全球资本主义来临的今天,似乎注定了它边缘的命运。“阶级”和“阶级压迫”这些50-70年代的官方概念,在《那儿》中获得了“现实对应物”。这套话语方式是否依然有着“意识形态询唤”的力量?也许我们不得不说,左翼文学一体化和体制化的时代已成过去,但是,它对现实的批评性和干预性,它关注时代、历史和底层的价值立场,它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呼唤,仍然彰显出它的价值。至少,我们看到,《那儿》的种种努力,为一种似乎已经死亡和已被淡忘的文学再次注入了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文学不死,左翼精神永存。
编辑:飞舟
来源:作者授权,原题“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新“左翼文艺”的力量——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
-
-
《黑&白》英文版问世
넶150 2025-04-22 -
预告|人境讲坛(2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改变世界
넶116 2025-04-19 -
预告|人境讲坛(18):“《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货色?”
넶172 2025-03-26
-
戈邓对话透视
넶14154 2024-08-07 -
邓小平80年代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넶11307 2024-09-13 -
【钩沉】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
他们不明白,如果不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继续进行斗私批修的社会主义革命,任由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党内一小部分领导人会蜕化变质,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成为新的资产阶级。
넶8507 2024-06-21 -
-
魏巍:论毛泽东晚年
넶4471 2024-08-27 -
孔庆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敢于战斗,善于战斗——纪念毛主席诞辰131年韶山讲话
넶3966 2025-01-07 -
刘继明:漫谈“革命文化”
넶3611 2024-08-21 -
评《望子成龙》:梦想在前,悬崖在后:谁为工人们“重头再来”埋单?
넶3296 2024-11-15 -
红贝访谈|纪念魏巍:反对修正主义民族主义
넶3261 2024-08-24 -
【人境论坛】刘继明|思想简史:一个时代的蜕变(2001-2021)
本文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笔者以个人和亲历者视角,对近二十年,特别是互联网兴起以来,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思潮,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蜕变过程,做出的一份有別于主流的观察记录。
넶2429 2024-05-29
-
《金光大道》读友群讨论会——会议记录(二)
넶15 2025-05-01 -
《新世说》组诗
넶9 2025-05-01 -
-
-
阿花(短篇小说)|人境院写研班学员期中作业选登(1)
넶9 2025-05-01 -
劳动节专辑③|有感于“五一国际劳动节”
넶12 2025-05-01
-
-
-
人境讲坛(17)|”人性自私论“为什么是错误的
넶101 2025-03-31 -
人境讲坛(16)|马克思恩格斯对亚当·斯密人性论的批判
넶72 2025-03-11
-
-
对《抨击南街村,既不道德,也缺乏理性》一文的回应
넶323 2024-11-16 -
南街村是“共产主义社区”吗?(下)
넶198 2024-11-16 -
南街村实地考察探析
本次参与讨论争鸣的包括左轮、雷骏和该文作者在内,都是向往真社的群众。因此本号希望对南街村的讨论不要简单贴标签对立为所谓的“抨击”或悍卫,而是应回归到对客观现实和未来方向的准确把握与思考上来。
넶208 2024-11-12
-
-
【理论与争鸣回顾】一场精彩的辩论:“纯左”VS“民左”
日前,在某微信群发生了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主要围绕近期在泛左翼阵容引起关注的“民左”之争展开,双方针锋相对,火药味甚浓,但除个别涉嫌人身攻击外,总体是理性的,充分表达了各自的立场。现整理出来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넶409 2024-11-14 -
-
【理论与争鸣回顾】刘继明:“民左之争”与左翼的困境——答滠水农夫和赤浪青年
文|刘继明
【刘继明按:因忙于长篇写作,近期很少上网。狂飚网的同志来微信说,“关于民左的争论已...넶493 2024-11-14
-
“司马南事件”透视——人境院第二届写作研修班第三次讨论课纪要
넶878 2025-04-17 -
司马南的教训是一记警钟
넶915 2025-04-08 -
【争鸣】把坏事变好事:从司马南事件看左翼和话语空间的困局
넶787 2025-04-06 -
司马南为何左右不逢源?
넶1732 2025-03-30
-
【新潘晓来信】血脉并不会像火一样灼灼燃烧,只有信仰可以燃烧
넶116 2025-01-17 -
【新潘晓来信】一位教培从业青年:无奈的人生啊,怎么越走越窄
넶99 2025-01-15 -
【新潘晓来信】一名失业青年的牢骚
넶160 2025-01-10 -
“新潘晓来信”征稿(第二期)
넶143 2024-12-23
-
完整准确地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 与李陀先生商榷
넶224 2024-08-06 -
李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条彻底回归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넶2418 2024-08-04 -
-
躲在唯心主义历史观小楼里的李陀
李陀先生应该感同身受。大概“不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在李陀那里也发挥着“二重性的直观”的作用,这些概念游戏可以帮助李陀继续躲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小楼里,让他感到安全、自在、和谐。
넶1048 2024-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