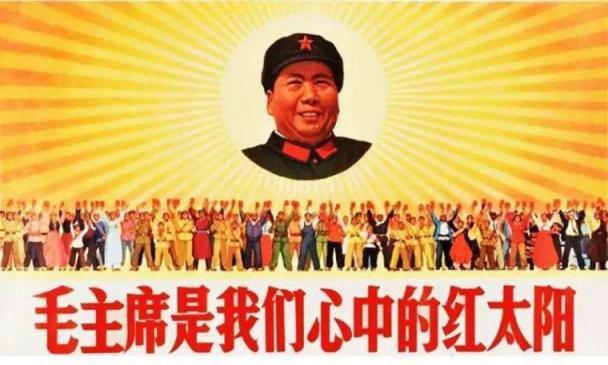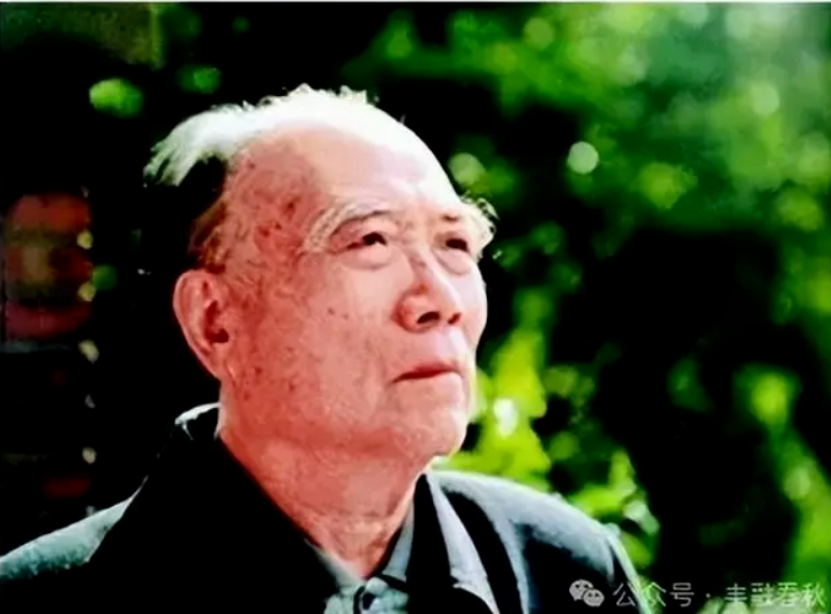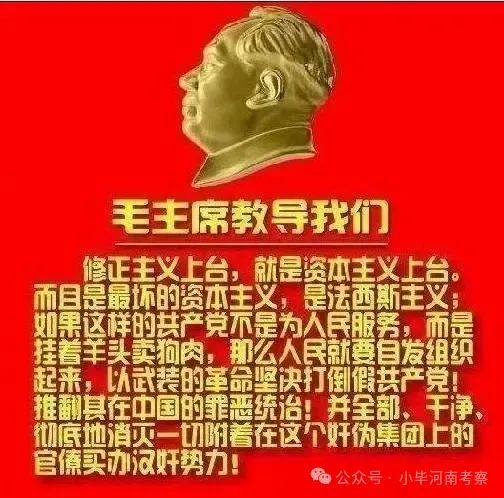革命者是这样炼成的——作为红色文学经典的《黑与白》|征文选登⑨
文\小毕(大学生)
一
什么是红色文学经典?
在我看来,红色文学经典就是能从中不断发现人类智慧与人本质的光辉的作品。人的智慧与人本质的光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人民群众的劳动中历史地产生的。这就是说,这种经典作品总是经过现实启发,并且进而启发现实的。我们能够在红色文学经典中发现劳动人民思想的智慧,而这种智慧也不断启迪一代代革命人民。
红色文学经典也可称为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经典,这是《黑与白》被称之为红色文学经典的原因,因为它是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因为它是维护现实的人的尊严,而揭露扭曲的、片面的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的。从这一点看,《黑与白》立足于现实人民的悲欢离合,并为中国人民做一份诚实的笔录。《黑与白》作为为劳动人民书写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人民的历史性遭遇的深刻总结,更是为历史的后继者提供的一份证词。
《黑与白》的历史跨度相当大,上起新民主主义革命,下至21世纪,脉络紧紧围绕着新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复辟问题。从这样的思路宏观地把握《黑与白》,我们就能得到一组二元对立,即革命者与复辟者的对立。革命者以王晟、顾筝、骆正、老校长、程国军等人物为代表,而复辟者则以武大师、杜威、宋乾坤、郎涛、洪太行等人物为代表。
倘若只是机械地走入这种二元的对立中,经典之内在思想精髓是无从发现的。必须从一种存在主义的角度切入,才能真正发现《黑与白》的思想价值。什么是革命者?革命者不是某些人生来的本质,革命者是通过革命的战斗才成为革命者的。这种存在先于本质的认识,恰恰是《黑与白》中一个个坚定的革命者们通过勇敢的斗争实践的。
二
王晟应该说是能引起许多人共鸣的角色了。王晟的父亲王胜利是一位坚定跟随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他给儿子取名为《英雄儿女》中的志愿军战士的名字“王成”。王成(王晟)生来就被父亲印上了革命年代的外在的符号烙印。对此时的王成(王晟)来说,这种革命的象征不是他内在的本质,而是外在的规定。这种外在的规定对王成而言不是发自内心的认同的,而是让他苦恼、让他觉得自己被孤立的。这种苦恼最终促使王成给自己改名。
没有人生来就是革命者,哪怕老爹老妈都是革命者,这种革命精神也不随着基因延续到下一代。王晟的改名就体现了这一点。“王成”这个名字,作为一个外在的符号,与其说真正把王成变成了一个革命者,不如说在王晟的内心种下了革命的种子。这种子,便在王晟历经了现实的变迁,包括遭到杜威出卖、加入大众艺术传媒集团、收到宗天一来信等经历后,终于破土而出。这就是直面现实:是帮助宗天一揭露黑暗,还是为了眼前的荣华富贵让朋友含冤而死。
当王晟毅然决然地与眼前的荣华富贵决裂,与同事的孤立冷眼,与杜威的威逼利诱决裂时,王晟为自己赢得了革命的存在。王晟不是因为生来的“王成”的名字,或者父亲孜孜不倦的灌输教诲而成为一个革命者的,而是王晟主动选择成为一个与黑暗现实决裂的革命者的。萨特强调: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王晟也是自由的,王晟自由到可以选择彻底决裂,不屈服于一切来自杜威和与他勾结的腐败分子的威胁,更自由到了他完全可以选择对真相视而不见,保存自己的荣华富贵。在这种自由中,王晟选择了最坚决的决裂。这种决裂,象征着王晟已经把革命精神内化为自己的目的本身。此时王晟真正理解了父亲,也真正成为了父亲期许的“王成”。
存在主义有个经典的命题:存在先于本质。王晟勇敢的存在创造了自己革命的本质。这种革命形式、革命符号在王晟内在的实现,真正塑造了一个久经考验,最终勇敢地接下革命旗帜的革命者王晟的形象。王晟的经历就是现实的人所赢得的辩证法的胜利。
王晟是中国人民的缩影。从一开始,王晟是被外在规定了一个革命的符号的。王晟对此不满,渴望冲破这种外在的规定。然而在历经了现实的斗争后,王晟最终决定以革命者、决裂者的方式存在。而这种存在最终促使王晟把曾经外在的、抗拒的革命符号内化为自我的实践。这就是一个潜在的革命者在现实的生活中,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最终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的历程的缩影。
如果说对王晟的考验最终把王晟淬炼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那么这种淬炼同时也体现在女主角顾筝身上。在《黑与白》全书走向最低谷的时刻,顾筝勇敢地站出来与整个法律系统,包括自己的老师、前辈、各种资源做出了决裂。这种决裂也象征着顾筝赢得了属于自己的革命的存在。
一个普通人究竟该怎样成为革命者?成为革命者不是脑子一热就瞬间完成的。刘老在《黑与白》中通过对社会变迁与人的自我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深刻洞察,给出了他的见解:人不是生来就是革命者的,人是在现实的斗争的磨练中,靠纵身一跃的勇气和毫不妥协的决裂而成为革命者的。
三
除了逐渐成长为革命者的王晟、顾筝等角色,另一群同样革命者也同样给予我们深深的感动。这就是以老校长、骆正、王胜利为代表的“老革命”们。
如果说王晟是逐渐成长为革命者的迷茫的青年人们的代表,那么老校长则展现了真正坚定的革命者是怎样在复辟者、反革命们的轮番打压下坚守自己革命的存在的。
老校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亲历者,他的亲人都死在了还乡团的枪口下。与王晟生在一个意识形态混乱、社会主义教育缺位的年代不同,老校长是在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长大的。人民政府的抚养、社会主义的教育使得老校长从《黑与白》一登场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这种共产主义信仰,支持着老校长在改革开放后对各种复辟分子和复辟势力的坚决斗争。
老校长是凤凰岛唯一小学的校长。岛支书聂长海是老校长最得意的学生。但是在聂长海蜕化变质,背叛社会主义理想后,老校长慢慢与聂长海决裂。在凤凰岛逐渐被开发为旅游岛的过程中,老校长不断领导村民与腐败分子抗争。而在凤凰岛民最终被迁走后,老校长又毅然决然地留在岛上守护烈士陵园:老校长用自己理想主义的抗争践行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
可是《黑与白》不是供人放松的爽文,而是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老校长拼尽全力的抗争,只是更沉重的展现了革命者们遭到反动派残酷镇压的冷峻现实——老校长的理想主义在最现实的反革命车轮下被碾过。在复辟势力从物质和精神双重的反攻倒算中,老校长孤独地死在凤凰岛上的老屋里。死的时候,桌子上有一本摊开的《共产党宣言》……这不是英雄浪漫的落幕,这是活生生的,最真实的残酷现实。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用坚定的信仰维护自己革命者的存在的现实。为了内心坚定不移的理想,即使是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这就是我们的老校长。在与复辟者、走资派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老校长燃尽了生命最后的火焰。读到最亲爱的老校长的去世,我当时抱头痛哭,现在提笔写作,更早已泪流满面。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老校长一生的真实写照。老校长是独属于劳动人民的感动。这样的感动同样表现在因为没有完成毛主席任务忏悔的砖瓦厂老厂长王胜利身上,也表现在坚持举报位高权重的革命叛徒走资派宋乾坤的老地下革命者骆正身上。在走资派的魑魅魍魉们的压力铺天盖地地压下来的时候,是他们挺起了共产主义者的脊梁,是他们坚守了革命先烈的英雄本色。
四
在王晟历经现实斗争而蜕变为革命者的时候,和王晟同龄的杜威、巴东却在历史的裹挟下沉沦为资产阶级复辟的排头兵。在老校长、骆正、程国军等革命者遭受现实的迫害压迫,依然坚持着共产主义光辉时,宋乾坤、洪虎等老革命却慢慢松懈、最终走向革命的反面。可见人是没有什么固定的本质的,人的一切就是人自由的选择。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者萨特的格言:“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
革命者不是生来就是革命者的,而是在革命的斗争中把自己实现为革命者的。对于走资派复辟者也是一样的道理。在《黑与白》中,王晟、顾筝、老校长、王胜利、骆正……这些可歌可泣的革命者角色,正是经过辩证的人的发展过程的中介,真正把自己实践为坚定的革命者。这不是简单的形式逻辑的爽文,而是对于人的发展的辨证规律的深刻认识。
《黑与白》正是建立于这种辨证方法的精髓上的。《黑与白》据此扬弃了长期贯穿于中国伤痕文学视域中的形式逻辑的宰制,真正在《黑与白》一书中实现了对人的本质、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文学观的复归。
《黑与白》真正站在了辩证法所统率的历史高度上。它所蕴含的对社会结构变迁(详见笔者《黑与白中的阶级复辟》一文)与人的本质的复归的反思,注定了《黑与白》实现了对人的智慧与人本质的光辉上现实认识。从这个角度出发,《黑与白》无愧于“红色文学经典”之荣誉。
编辑:红日欲出
来源:人境网
-
-
《黑&白》英文版问世
넶149 2025-04-22 -
预告|人境讲坛(2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改变世界
넶115 2025-04-19 -
预告|人境讲坛(18):“《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货色?”
넶172 2025-03-26
-
戈邓对话透视
넶14151 2024-08-07 -
邓小平80年代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넶11305 2024-09-13 -
【钩沉】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
他们不明白,如果不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继续进行斗私批修的社会主义革命,任由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党内一小部分领导人会蜕化变质,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成为新的资产阶级。
넶8502 2024-06-21 -
-
魏巍:论毛泽东晚年
넶4471 2024-08-27 -
孔庆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敢于战斗,善于战斗——纪念毛主席诞辰131年韶山讲话
넶3965 2025-01-07 -
刘继明:漫谈“革命文化”
넶3611 2024-08-21 -
评《望子成龙》:梦想在前,悬崖在后:谁为工人们“重头再来”埋单?
넶3294 2024-11-15 -
红贝访谈|纪念魏巍:反对修正主义民族主义
넶3259 2024-08-24 -
【人境论坛】刘继明|思想简史:一个时代的蜕变(2001-2021)
本文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笔者以个人和亲历者视角,对近二十年,特别是互联网兴起以来,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思潮,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蜕变过程,做出的一份有別于主流的观察记录。
넶2429 2024-05-29
-
读《两个朋友》与《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比较两篇小说中人物刻画的艺术手法的不同
넶27 2025-04-30 -
-
无产阶级革命和所谓“左圈”人士
넶57 2025-04-30 -
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넶26 2025-04-30 -
那年,我被学校“卖”到了酒店
实习工资一个月1600块,实习时间一般为一年,同工不同酬,美其名曰“产教融合”。我发现是被“卖”掉了,学校卡毕业证,酒店卡实习鉴定表,学校、酒店吃人不吐骨头。涉世未深的学生还没毕业就有这么大的教训,让我着实难忘。
넶91 2025-04-30 -
革命者是这样炼成的——作为红色文学经典的《黑与白》|征文选登⑨
넶24 2025-04-30
-
-
-
人境讲坛(17)|”人性自私论“为什么是错误的
넶101 2025-03-31 -
人境讲坛(16)|马克思恩格斯对亚当·斯密人性论的批判
넶70 2025-03-11
-
-
对《抨击南街村,既不道德,也缺乏理性》一文的回应
넶322 2024-11-16 -
南街村是“共产主义社区”吗?(下)
넶197 2024-11-16 -
南街村实地考察探析
本次参与讨论争鸣的包括左轮、雷骏和该文作者在内,都是向往真社的群众。因此本号希望对南街村的讨论不要简单贴标签对立为所谓的“抨击”或悍卫,而是应回归到对客观现实和未来方向的准确把握与思考上来。
넶207 2024-11-12
-
-
【理论与争鸣回顾】一场精彩的辩论:“纯左”VS“民左”
日前,在某微信群发生了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主要围绕近期在泛左翼阵容引起关注的“民左”之争展开,双方针锋相对,火药味甚浓,但除个别涉嫌人身攻击外,总体是理性的,充分表达了各自的立场。现整理出来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넶409 2024-11-14 -
-
【理论与争鸣回顾】刘继明:“民左之争”与左翼的困境——答滠水农夫和赤浪青年
文|刘继明
【刘继明按:因忙于长篇写作,近期很少上网。狂飚网的同志来微信说,“关于民左的争论已...넶491 2024-11-14
-
“司马南事件”透视——人境院第二届写作研修班第三次讨论课纪要
넶875 2025-04-17 -
司马南的教训是一记警钟
넶915 2025-04-08 -
【争鸣】把坏事变好事:从司马南事件看左翼和话语空间的困局
넶782 2025-04-06 -
司马南为何左右不逢源?
넶1727 2025-03-30
-
【新潘晓来信】血脉并不会像火一样灼灼燃烧,只有信仰可以燃烧
넶116 2025-01-17 -
【新潘晓来信】一位教培从业青年:无奈的人生啊,怎么越走越窄
넶99 2025-01-15 -
【新潘晓来信】一名失业青年的牢骚
넶159 2025-01-10 -
“新潘晓来信”征稿(第二期)
넶143 2024-12-23
-
完整准确地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 与李陀先生商榷
넶222 2024-08-06 -
李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条彻底回归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넶2417 2024-08-04 -
-
躲在唯心主义历史观小楼里的李陀
李陀先生应该感同身受。大概“不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在李陀那里也发挥着“二重性的直观”的作用,这些概念游戏可以帮助李陀继续躲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小楼里,让他感到安全、自在、和谐。
넶1048 2024-07-24